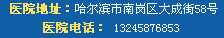文/刘裕国、郑赤鹰
从泸沽湖往西,翻过狮子山,很快就进入木里县境。木里的景色与大凉山迥然不同。高大的山峰,一座一座,傲然耸立,相互不买账的样子,不像我们经过的大凉山的山那样,一座连着一座,挤在一块儿——我们曾经以为是错觉,后来,木里县的同志告诉我们,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。因为木里河流深切,岭谷相对高差很大,全县形成三个大地貌,即西北部的山原地貌,东南部中山深切割山地貌和西南部的高山深切割山貌。全县整个地势南倾,主要河流沿断层由北而南,流入金沙江,并与四条南北向的山脉相间排列,构成了木里藏族自治县地貌的主体,属于典型的高山、山原、峡谷地貌。
公路两旁的植被也与大凉山不同。大凉山的植被也是相当好的,放眼看去,郁郁葱葱,只是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,那些植被大都是人工造林的成果。木里却不同,路旁的树木粗壮高大,而且还挂满了丝丝缕缕浅黄色的长须——当地人把它叫作“树胡子”,学名松萝。松萝只能攀附在树上生存,对环境要求零污染,只要有一点污染就会变黑,慢慢死亡,因此可以当作天然环境污染检测器,由此可见木里的环境何等清新。
木里为世人所知晓,不能不提到一个美国人类学家、植物学家、纳西文化研究家约瑟夫·洛克(—)。洛克生于奥地利维也纳,年开始自习汉文,年入美国国籍,年为夏威夷学院植物学教授。从年起,先后6次到中国,3次到木里。他在《中国西南古纳王国》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谈及盐源县的历史和地理——其时,木里归盐源管辖。后有专著《中国黄教喇嘛木里王国》问世,详细记载了木里的风光、人文、地理以及他在木里的亲身经历。英国人希尔顿正是根据洛克的描述,创作了《消失的地平线》。
藏传佛教寺庙的金色大顶,高耸入云的皑皑雪山,褐色屋顶的古村落,还有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与湖泊……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,如何用好呢?木里人别出心裁,以线带点,以点带面,打造四种颜色的钻石旅游线路:金色,以18座大小藏传佛教寺庙为主,其中木里大寺供奉的28米高的镏金甲娃强巴佛是当今世界室内镏金强巴佛铜像之最;白色,以雪山为主,恰朗多吉雪山、贡巴拉神山、麦地贡嘎神山……其中,恰朗多吉雪山在世界佛教24圣地中排第11位;褐色,以古村落为主,古老的亚英藏寨、俄亚纳西古寨、利加咀母系部落、项脚明清汉遗民村寨,多姿多彩;绿色,以原始森林与湖泊为主,木里是中国活立木储量第一县,森林覆盖率达到67.3%,红豆杉、云杉、雪松、岩柏组成的浩瀚林海遍布县境。
为了保护这片绿色的土地,木里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年3月30日18时许,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雅砻江镇立尔村发生森林火灾,着火点在雅砻江边,距木里县城车程6—7小时,火场平均海拔米,多个火点均位于悬崖上,地形复杂、坡陡谷深,交通、通信不便。年3月31日下午,扑火人员在转场途中,受瞬间风力风向突变影响,突遇山火爆燃,部分扑火人员失去联系。4月1日晚,经全力搜救,30名失联扑火人员已全部找到,27名森林消防队员和3名地方干部群众牺牲。牺牲的27名森林消防指战员平均年龄只有23岁。45岁的木里县林业局局长杨达瓦算是年纪比较大的,儿子正在读大学。在林业部门,护林防火是头等重要的工作。每年春节前开始,干燥的风从雅砻江河谷中刮过,带走森林中的水分,一个小火星,就能引发一场大火。杨达瓦经常因此出任务。3月30日,杨达瓦原计划去西昌开会,火灾发生,他掉转车头,上山灭火,这次,他再也没能回来……
火灾之后,全国各地捐款捐物。其中最大的一笔捐助来自广东佛山。在佛山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亲自安排下,佛山拿出万元,紧急购置了台配置最高的福田皮卡车,赠送给凉山州各县。4月中旬,这批皮卡全部运抵凉山,连夜开赴各县乡镇。
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是四川和云南共同打造的旅游区,木里地处这个旅游区的核心区域。木里对此极为珍惜。他们把旅游扶贫作为重点,由县国资委牵头,集合贫困村的产业基金,在旅游热点地区盖起了3个星级宾馆;全县个村,全部按6.5米宽的旅游道路修通硬化路;国家电网和4G信号覆盖了所有村子;县里还打造了一批旅游扶贫重点村,建设旅游驿站、乡村民舍,其中有4个示范村,利加咀就是其中一个。
我们驱车沿省道直奔位于木里南端的屋脚蒙古族乡。沥青路面十分平坦,车子跑得很是轻快。驰离省道之后,进入了一条崎岖的山路,颠簸了很久,才来到利加咀。
这是一个名字很土,但景色很仙的地方!四周群山环绕,地势险要,山高平均在海拔米左右,中间是低平开阔的平坝,平坝长度直径不足1公里,呈椭圆形,达卡布沟河流经该地,高山、草甸、花海、溪流,汇成一幅清新脱俗的美丽图画。也许,正因为交通闭塞,才使生活在这里的摩梭人得以保存独特的文化传统,这里是中国最原始、母系文化保存最完整的部落。木里县文旅局副局长冬嘎珠扎告诉我们,在这个母系氏族村落,近人分属于26个家族,家中由女性主事,家庭成员只有母系的姐妹兄弟及其子女。母系姐妹子女的父亲属于另一个家庭的成员,母系氏族至今实行“走婚制”。女性在家庭中占主要地位,家庭里的成员都是一个母亲或一个祖母的后代。家庭中无男子娶妻,无女子出嫁,始终生活在母亲身边。财产按母系继承,家庭成员的血统完全以母系为准。
天色已晚,我们一行人在利加咀住下。村里人住的都是封闭式的四合院两层木屋。祖母屋通常设在一层。祖母屋的这一排称正房,正房对面为二层楼,叫女楼,楼上主要供成年女子居住,女子要到13岁举行穿裙礼后才能单独有自己的女室。传说中的爬楼梯、敲门、走婚就发生在女室。通常情况下,成年男子是没有自己单独房间的。
出乎我们意料的是,我们几个人的下榻之地,居然是三幢独立的、圆木搭建的小别墅。以木制屋,就地取材,天然环保,避免污染;此外,较之砖石结构建筑,木质房屋又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抗震作用。更让我们吃惊的是,并排的小别墅前方,还有一栋三层高的建筑,利加咀传统建筑风格是封闭四合院木屋,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建筑呢?
主人家领着我们参观,原来,这栋楼是一个民宿客栈。一楼、二楼是单人间或者双人间,三楼则是一个打通的大开间,有点类似会议室,中间摆着一张大桌子,四周是长条靠椅,推开木楔固定的雕花窗,晚风吹来,带来一丝丝甜甜的清香……
另一个出乎我们意料的是,这个主人家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祖母或者母亲,而是一个身材瘦削的摩梭汉子,41岁的杜基。
杜基家兄弟姐妹8个,杜基是老五。现在和两个姐姐、一个妹妹及舅舅住在一起。按照摩梭人的习俗,家里管事的是祖母、母亲,祖母和母亲不在了,舅舅为大,舅舅做主。可是,杜基的舅舅岁数太大了,比杜基整整大了三番。在摩梭人的算法中,一番是12年,也就是说,舅舅已经77岁了,每天,除了戴着水晶太阳镜晒太阳,已经做不了什么事了。两个姐姐没有读过书,杜基在外边打过工,有见识,有胆略,家主的担子只好由杜基挑了起来。
杜基从接手家主的那天起,就萌生了一个想法:盖一个大大的民居。
那时候,利加咀已经名声在外了。4年,钱钧华写的《女人国:中国母系村落利家嘴》一书出版,引起很大轰动。作者长期潜心研究人类早期习俗以及当代社会问题,《女人国:中国母系村落利家嘴》就是作者在利加咀实地采访写成的专著。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及在当地拍摄的真实照片,介绍了利加咀独特的风俗习惯和母系文化特征,包括他们的饮食起居、家族结构、血缘伦理等等,讲述了许多利加咀人的真实故事。
一位书评人这样评价道:来到举行葬礼的山坳,我的心很静穆。面对新鲜着和腐朽着的五彩缤纷的经幡,面对一堆黑色的灰烬和残剩的没有燃烧完毕的木柴,面对祭祀用过的酒杯、碗盏等等,眼前似乎有若干个化为青烟的灵魂在上下翻飞。我突然感到应该更新审视并领悟生命。
7年,村里发生了一件大事:一位香港女教师倾心于摩梭文化,钟情于利加咀村村民乔子平措,住进了利加咀村。
不久,两名德国艺术家来此进行摩梭文化展览和策划筹备。在香港女友的支持和村民的反对声中,平措决定把自己家里的祖母屋作为展品出售给他们。
年4月15日,这座有近百年历史的摩梭祖母屋被编号、拆卸,经由丽江、昆明运往北京。这年5月,平措家的祖母屋在北京市朝阳区环铁艺术区9号院被重新拼装并隆重展出。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,平措利用卖房所得资金前往永宁聘请摩梭老木匠,按照摩梭传统,在原址建起一座规模更大、文化要素更加典型的摩梭祖母屋。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千里迢迢来到利加咀的人越来越多。人来了,就要有地方住啊。杜基先是把自己家的房间腾了几间出来,接待外来的客人。可是,来的人太多,房间根本不够用。于是,9年的时候,他把部分老房子拆掉,用两万元钱,盖了几间新的,专门用于接待客人。可是,还是太少,不够住的。他想,为什么不盖一个大一点儿的旅馆呢?他想象中的旅馆,最少应该是三层楼,有三四十间房,还应该有一个大的会客厅,大家可以在一起喝茶,一起聊天,一起唱歌……
不过,这可是一个大工程哦!没有几年工夫别想完成!宅基地倒是有的,可是,在利加咀盖房子,总不能盖砖瓦房吧,按传统,得盖木头房,需要大量的木料吧,每家每户每年的木料是有限额的。怎么办?村委会干部听说了,主动提出,给他们家调剂木材配额,每年增加一些。
当然最关键的是缺钱。没办法,只好先赊账了。房子的墙可以用木头,房间里面,像卫生间还是要用瓷砖的,还有门啊、窗啊,都要用雕花木板,都要用钱啊!杜基经常跑的市场是云南永宁镇,骑摩托车要跑1个小时,那儿做生意的大都是摩梭同胞,信得过,赊个两三年没问题。日复一日,月复一月,杜基就像筑窝的燕子一样,把各种建材一点点地往家搬。
他也知道这是个大工程,必须发动全家人一起参与。家主发话,兄弟姐妹挣了钱,每年都要把大头拿回来,用于建房。家主说话,兄弟姐妹还是很听的。不管挣多挣少,每年都要拿回来一些。虽然离杜基想象的还差得很远,但是,离他的梦想总归越来越近了。
木里县文旅局听说了这个事儿,很是重视,他们文旅局正好也是利多咀村的帮扶单位。副局长冬嘎珠扎是个非常耿直的藏族兄弟,他了解情况之后,报告到县里,县里一次性补助了杜基5万元钱。这5万元可是解决了大问题,替杜基还掉了很大一部分债务。
话说这是年的事儿了。
一天,杜基家来了几个做大学问的人,被杜基家二楼上的两幅壁画迷住了,他们如获至宝,拿出放大镜,仔仔细细地端详。两幅壁画色彩斑驳,还是能看出人物山川的轮廓,画工十分精细。
他们问:“这个壁画有年头了吧?”
杜基说:“是,有两百年了。你们去过木里大寺吧,离这里里路。两百多年前,修木里大寺,来了很多大工匠、大画师。木里大寺修好了,我们家的老祖宗请了两位为木里大寺画画的大画师,在这儿画了一两个月呢!”
“这可是非常珍贵的文物,要保护好哦!”
坐在天井里,他们一行人喝着酥油茶,仔细倾听杜基的打算,很是赞赏:“杜基,有志气,好好干!摩梭文化是一个宝藏啊,我们要好好宣传,让更多的人来看,来了解。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。”
临走,人家还再三叮嘱:“建民舍,要保持摩梭的原汁原味,有的民舍用了琉璃瓦,亮闪闪的,太刺眼了。”
杜基说:“我们已经定了,用土瓦的。”
杜基家三层楼的民宿是年底盖成的,主体工程算是完工了,围墙、小广场还有一些附属工程远没有完成,总算可以开门迎客了。对于那些不远千里,自驾或者徒步来到利加咀村的人们来说,能住上这样的民宿,真是喜出望外。不经意间,杜基成了“网红”。客人们在网上晒图,晒这个藏在深山里的民舍,晒一日三餐的美食,还专门注明,大厨就是杜基的妹妹,在乡政府组织的新型农民工素质提升工程中参加过厨师培训的。早餐,想吃稀饭、面包,还是面条、酥油茶,杜基会征求意见;午餐和晚餐,杜基会先敬酥油茶,再敬青稞酒,菜有荤有素,鸡是杜基家自己喂的,猪是杜基自己养的,梨儿都是刚从树上摘的。除此之外,还出售手工织成的毛毯、腰带、摩梭人的全套衣服等等,这是杜基的姐妹们亲手织的……
这样的结果就是订单源源不断,回头客越来越多。
我们问过杜基:“前前后后,投了多少钱盖民宿呢?”
杜基憨厚地一笑:“哎,真的没办法算,也记不清楚了。”
“那你这民宿怎么收费呢?”
“看人家的情况呗。学生娃嘛,有多少给多少,收过40元一天的。现在,一楼的双人间,80元;二楼的单间就是元啰。”
他的回答,非常符合摩梭人的习性:钱不重要吗?重要!但是,钱不是所有,更不能代表一切。杜基知道,他们村子里,亲戚也好,朋友也好,乡亲邻里也好,从来没有闹过经济纠纷。这是摩梭人的传统。
我们忍不住好奇,问杜基:“这么些年,有没有爱上哪个摩梭姑娘?”
杜基羞涩地摇摇头。
“有没有摩梭姑娘或者别的姑娘爱上你呢?”
他还是摇头。
“不会吧,你这么帅的一个男子汉哟。”
杜基笑笑。
我们也没有再问了,谁的心里没有一个小秘密呢?我们只希望,杜基在这个小小的母系社会里,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位置,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幸福。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abmjc.com/zcmbyf/3077.html